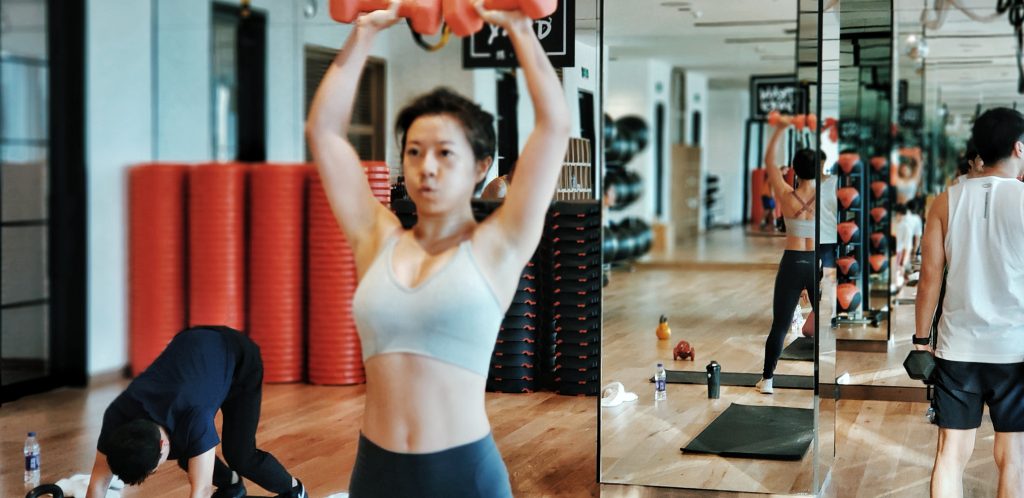让我先喷一喷
接着上篇文章说,姜文和周韵的关系的核心架构发生在婚姻法项下
你看,一个工业时代的产物越来越无法承载一个现代社会实际发生的东西,姜文和周韵的关系是一个天然发生的错综复杂的关系,但它涉及婚姻法、公司法、劳动法,还有更多其他的东西,等等等等,它倘若是只在婚姻法项下,则一定不如现在这般好,工业社会的所有产品,都是一把刀子,切开了真实发生的事情,工业社会的所有概念和手段,都越来越无力,正在消亡过程中
婚姻法把一个本来在发生的东西给用小刀切割了,你非要一个更高维的东西按照一个被切割了的低维的轨迹去跑,这压根不make sense。就像是你非要一个11维的智子跑一条卡丁车赛道,那这智子肯定跑不好,跑着跑着就得偏航,这智子如果脑子想不明白,就得觉得自己怎么老是跑偏,是不是得调整,这一调整就浑身上下都膈硬。其实智子应该想,我尼玛比你赛道高级8个维度好嘛,我按照你的轨迹跑不好,是因为你不如我高级,要改变的是你这个低级的赛道,而不是我的轨迹,我take over the world的时候,你赛道都不知道还在不在了
姑娘们,你们比婚姻法更高级好吗,高级好几维
但是有一个思路就是压根不对的了,比如,因为婚姻是两个人的亲密关系,所以你要找一个亲密关系中能够相处的,这是用一个低维逻辑去给高维的东西设置条件,最终低维逻辑会更快消亡,被高维逻辑替代。是的,大家现在甚少按照“因为我要结婚,所以条件是xxx”这样的逻辑去选择另一半,但是婚姻这个错误的切割的刀子存在,这个过时的标准样品的存在,误导了人们的选择逻辑
以上是接着上一篇的喷,下面是本文核心,hoho
山河并肩坐着
在我刚刚进入社会的时候,见过的夫妻,挺大的影响了我,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潘石屹和张欣
我记得我们跟soho做一个CB可转债,时间表很紧,有天早上我们跟张欣开会,她坐在我对面左边斜前面,中间潘石屹走进来,他们俩递了一个眼神,眼神里充满了合伙人之间的默契、快乐。因为要在一周之内把可转债发行完毕,所以那5天我们投行是每天只睡两个小时,而张欣是陪着我们随时standby,我们什么时候ready要开电话会了,哪怕凌晨两点,都跟我们开怒长的电话会,一个一个很细的过条款,一点都不含糊。我见过的CFO们,吃里扒外,假公济私,不坑老板就不错了,哪里有这么尽职尽责的,能尽职尽责到这种亲妈程度的,那都是真的亲妈。Soho中国的上市也是蔡洪平做的,Soho的法律结构非常干净,每个项目公司全都在一开始很干净的搭到了海外,项目上的同事们都开心死了,相比其它一摊烂帐、需要花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收拾架构和财务的民企,你看,这就是ex高盛的手笔
在很多年以后,他们二人那个默契的眼神还常常盘旋在我的脑海里,要知道,那时候他俩已经结婚约15年,在我见过的老夫老妻里面,真的很少见过这么正面的两个人的默契,你幸福与否默契与否这是伪装不来的,一个眼神就看出来的,两个人之间的chemistry是装也装不出来。是的,潘石屹张欣他们各自都有表外资产,都有法外结构,但是so what呢,说得好像其他夫妻没有一样,就好像其它表面上没有的夫妻实际上不是拧巴着的一样。当18个月的化学元素激情过去,所有关系都会掉入一个别的什么,有人掉入柴米油盐,有人掉入无休止的争执,有人掉入冷漠,幸运一点的掉入搭伙养小孩,或者一个人付钱让另外一个人养小孩,这些,还不如掉入一起做点事儿呢不是吗?
我知道潘石屹和张欣不是这个世界里普通的一对夫妻,他们不能作为普通人婚姻的模板,但是,我只能说,我见过这些东西走到终点的时候的样子。以及潘石屹张欣不是个案,老蔡经手过的那些个首富们,其老婆们大概率都在事实上扮演了关键的合伙人的角色,我可以说这就是模板,不是个案。换句话说,现在大家没有按照潘石屹张欣的底层逻辑去婚恋,是因为升级打怪还没有走到那里,等走到的时候,还是会使用和他们一样的结构。历史总是重复的,看潘石屹张欣的婚姻,和看历史书是一个道理,你可以不看历史书,用自己的肉身去试错,最后不过是发现,自己用自己一生的代价去尝试,最后无非就是证明历史书上已经告诉你的规律是对的而已。我的想法和别人不一样,不是因为我错了,而是因为我见过这一切到了终局时候的样子,别人没见过,我没有必要因为别人不认同我而改变我的看法
我认为人类获得长久快乐的唯一的方式是利他,是work on something greater than ourselves,婚姻关系的幸福也是,如果一对夫妻没有那机会或者没有那觉悟,那就要通过宗教,通过一个创造出来的神的故事去access to something greater than ourselves,每个周日去见一下上帝,打一下鸡血,用以让本身设置就有问题的婚姻再延续一周;如果有机会或者有觉悟,那就是一起做一件greater than ourselves的事情(当然,科学研究的结论是,决定快乐的50%是基因,10%是发生的事情,40%是exercise for something,与利他不冲突)
So,
总结来看,我喜欢的亲密关系是,互相开启,彼此成就,让对方变成更好的自己,给予对方支持在同一个方向上做事情,这肯定不是像潘石屹张欣做那么大,也不一定是做同一件事情,但是一样的底层逻辑的
我喜欢这样的关系,在我往前行走的路上,有一些人与我同行,有的人恰好成为了我的另一半,如果没有成为,那就继续在一样的路上往前走,另一半的关系也许很久,也许短暂,只是在同行的路上的相对位置关系拉近和拉远而已。它是天然的,不是被婚姻法这个刀子切割后的选择,我不会因为婚姻去diverge from my route – life is too short for this kind of waste
在所有的关于婚姻的意象里,我喜欢的是“山河并肩坐着,聆听幸福的声音”,是并肩看着一样的方向,是山河的大格局大叙事,是互相支持的整体,是宁静的是简单的是隽永的
以上是我的婚恋观